为了找回生活的意义,我搬去了大理
文艺青年集散地、中产阶级旅居区,大理如今的“网红”面貌已经360度无死角地代言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垂涎——古城山水如画、僻静疏远,与城市迥然不同,太适合在竞争丛林里寻求“中场休息”的人歇歇脚,喘口气。尤其二三十年前,这里作为由第一批新大理人亲手搭建的“乌托邦”,收留、滋养了太多有趣的嬉皮灵魂,“地不自灵,因人而灵”,在这里与谁碰个面、聊一聊,说不定就成为人生顿悟的引——至少,我们都是这样渴盼(幻想)的。
不久前,前《国家地理杂志》记者黄菊出版的《大理访谈录》,便对话了14位正在大理生活的“先锋人物”——举家搬迁的旅行作家、隐遁山林的高学历僧人、实践自然农法的日本家庭、崇尚手艺的书店老板、诗人和画家、电影导演……关于他们是怎么来到大理的,在大理经历了什么,为什么至今没有离开,均有解读,关于大理如今新的面貌和风评 ,也有自己的看法。
总之,读过这些故事,我们似乎能明白,“逃离北上广”,“去大理”,不仅仅必备风花雪月的情怀、浪漫的体质、充足的“消费成本”,还需得有强盛的精神指引和行动力。无论如何,作为内心那一小片,甚至最后一片自留地,我们依然继续向往它。
01
“我们这儿的日子,是无事常相见”
(许崧,旅行作家,定居大理10年)
2010年,我要找个便宜的地方写字,就来了大理。后来,半年里认识了半城的人。决定住下来,这是唯一的原因:人。这里的人相处的方式别处没有。
大理是个真正有社区的地方。传统乡村是有社区感的, 大家谁都认识谁,标准的熟人社会,而大理的新移民来自五湖四海,以前干什么的都有,它的多样性是传统社区无法相比的。我们一直说大理社区的本地文化基因是嬉皮文化,生活方式自由,平等,互相尊重,多样性丰富,很草根,节俭,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太能够做到的。在大理,一桌上吃饭的人可以从亿万富翁到赤贫者,社会形态呈现惊人的扁平化。大家的相处和不相处不是因为你的财富头衔和社会关系,只是因为你是你。

许崧和女儿月亮
大理社区的价值观核心是生活,这是相对于外面的“成功”主流价值观而言的。居民们自发成立了机车小组、登山小组、读书小组、帆船小组、滑翔伞小组、夕阳红篮球小组、烘焙小组,以及生娃小组、打毛线小组、观鸟小组等等。去年春节,一群艺术家、作家、诗人、导演、摄影师、书店老板和杂货铺老板,甚至自己排了大理版话剧《茶馆》,公映现场据说来了五百多位乡亲……这是以生活为根本重心的一群人。大理是个摆个摊也能活的地方。大理社区的本底,有一项就是不物质。我2010年到大理的时候,每月生活费,连吃带住带抽烟,一千块。房租低的时候,很多人开些稀奇古怪的店,随时就关门出去玩,大家拿个粉笔写什么“西坡的花又开了,出去闲散三天”,“陆地主来了,陪陆地主吃饭去”……门一关就走了。追求好生活,而不是追名逐利,就分开来大理和外面的世界。
我以前住在洱海门外的大院子村。那时候大家茶余饭后没事就上人民路一趟,就会遇见无数熟人,各种朋友开的店。我到大理的前三年,在人民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,到处点头,各种人招呼你喝茶,大家这里坐一坐,那里聊一聊,你把整条街都当做一个主场,一个会客厅。就像蔡澜先生书房里挂的条幅“只愿无事常相见”,我们这儿过的日子已经是把“只愿”拿走,已经是“无事常相见”了。
所以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,连那样的城市都不待,移到大理来生活,而且被它迷住,像我这样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定要问,出了什么问题?找答案的过程中,我发现,不是因为苍山,不是因为洱海,也不是因为这里的气候,就是因为人的关系。幸福指数高的人,都以一种“交流”的方式活着,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现代化的发展速度,把城市变成了一种隔绝人的地理环境,而这样的小城镇,是把人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地方。
02
“你看那个黑黑的就是洱海,我每天就这么望着红尘”
(林向松,兰若居士,定居大理9年)
我随母姓,客家人。我从小被教育周边都是神,日常生活都跟这些神明有关,尽管中途读高中,读大学也迷失过,但还是敬神的。我选择在山里,是因为现实中这么多年也到处碰壁,只能去寻找另外一条道路,让内心得到安宁。
大庙我看过和待过不少,觉得大多喧闹,人事复杂,所以就往云烟起处、深山老林里寻找机缘。大理这里都是一些基本上没有香火的村庙,人少,却清净,能安顿下我这个无处可依的孤魂野鬼。

林向松所在白雀寺,在苍山海拔2700米的山林里
你不知道那种惊喜,我在山林里就不愿意出来,山林的美,无法用言语形容! 只有两种人真正耐得住山:有诗意的人,有坚定信念的人。 我偏于前者。有一句诗说:“不给春风留颜色,誓与白雪埋一堆。”我不给春风留颜色,不跟世俗之人沟通,不融于世态,也不被世态所融,只有天天守山。你看那个黑黑的就是洱海,我每天就这么望着红尘。
一个人住在山里,最初还是有一点恐惧。野猪经常跑到我门口,带着他一群孩子,把我吃的东西全部搞完,那种野猪这么大一个,獠牙这么长,不害怕吗?后来我念《大悲咒》,慢慢就好了,现在我已经和山林融为一体。
我是一个读书人,早晨四点半摸黑起来烧香,把院里油灯点亮,然后晨钟也敲响了,我也开始做早课,四十分钟。晚上没有电,我会点着蜡烛读一段书,或者读一段经文。傍晚念经时,如果外面有彩霞,我会说:“菩萨,你等我一下。”就放下经去拍照片,拍完再回来继续念。我相信菩萨不会怪我,他也知道我太落魄了。苍山是一座神山,所谓的“耶稣光”“丁达尔现象”,我认为都是神光,要有风,有雨,有云,有雪,有光,有彩虹,才是神仙。苍山什么都有。
03
“有地,有房子,没什么钱,但是很舒服”
(辽太郎,日本千叶县人,定居大理8年)
大理是第一个我待了一年以上的地方。我待过的地方都很好,日本那边的农村也很好,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一起生活的人,还是一个人,还是想旅行,还是想出去。2011年,我去泰国学按摩,遇见了我的妻子。我想去西藏,所以从泰国骑自行车到大理,当时我问了很多人,都说西藏外国人不能进去,于是就留在大理。
我搬来两年半了。当时没有电,所有电都是自己通的,水有很多,这个村里的自来水可以直接喝,而且很好喝,花花草草也是慢慢弄的,房子里面取暖的炉子都是自己做的,石头墙壁也是自己做的。
我家里有差不多两亩的地种水稻、麦子,还有七八分地种菜。稻子生活空间要大一点,要不然风一吹,他们相互摩擦,会不舒服不开心的,不开心的稻子是长不好的。我们一般是自给自足,吃的都是自己种的,酱油、味精、醋、酒都是自己做的,吃不完就在外面卖,有时候去柴米多市集里卖菜,还有一些客人来我家买。我卖的菜是每天早上现摘的最好的菜。我们要卖好的东西,但是没有很贵。在中国,好的东西就贵,我不喜欢,我喜欢让一般的人也能吃,不是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吃。

辽太郎在大理种田
我的老家在农村和城市中间,小的时候也不管什么吃的东西。十八岁以后开始旅行,在一些地方做种种地的工作赚钱,发现吃的东西很重要,如果你吃好的东西,你的身体也健康,于是我想自己种吃的,就去学习怎么种。种地的话,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安排,但有些时候锄草、插秧、收麦子,我太太也一起做,孩子也一起来。以前农民的生活方式都是这样的。其实我们过得很简单,就是以前老农民那种生活,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,现在这样的人少了大家觉得很特别。

辽太郎和妻子阿雅,以及三个孩子:和空、天梦、结麻
其实是缘分,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,我来了这里就有了工作可以赚钱,有了朋友,有了地方可以睡,这些不是我自己找的,所有东西都自然而然地从外面进来,我就感觉应该留在这里。现在我在家里有很多事情做,有地,有房子,有孩子,没什么钱,但是很舒服,就是简单生活。
04
“在大理,大家吹牛的时候,都是宏大叙事”
(阿德,书店老板,定居大理8年)
真正决定来大理是2012年5月,那一年我女儿出生,想要有一个干净的环境。刚好一直想开一家书店,来大理看了一下,租金便宜,人民路上的店铺,一年房租一万八,这种机会还不来?

大理著名的独立书店,海豚阿德书店
大理这几年,认识了很多新朋友,见识了很多新活法,他们都是不为匆忙路过的旅客所知的。后来接触到更多的人,因为感情破裂、生意破产等等原因,陆续离开大理。有些人可能再不会回来,有些是想出去挣了钱再回来……我也想过逃离大理,觉得大理不够有趣了,但是因为做“大理百工”这个民艺调研项目,采访了一批手艺人,至少这几年是没办法离开了。
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大理剑川县沙溪镇有一对兄弟,他们有一个姑奶,非常有艺术天分,会各种各样的手艺,七十年代左右借住在他们家。两个小孩那时10岁左右,一天到晚在玩,姑奶就说:“我教你们每人一样东西,你们自己选。”结果哥哥就选了纸花,弟弟选了剪纸。那个东西真的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。现在周围只要有结婚的,都会用到他们哥俩的东西,剪纸的“喜”字贴在堂屋里,纸花就做婚礼现场装饰……我还采访了一个木匠,他是哈佛建筑系毕业,九十年代就设计了鸡足山最大的寺庙的大雄宝殿,他带我们去看,说这是我修的,旁边有一个钟楼和鼓楼是他父亲在八十年代初修的,两代人的东西,在那个地方相互对望着。
你知道,在大理,大家吹牛的时候,都是宏大叙事,但是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手艺人,而且全都是在地的东西,你会发现这个大理跟你当时来的那个大理是不一样的。我以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,所以会去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你看过伍迪·艾伦的电影《无理之人》吗?那个哲学教授通过杀人来寻找生活下去的意义,而我,通过“大理百工”找回了生活的意义。在现在这种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,好像只有手艺,一两百年都没有任何变化,这是很难得的。
05
“去大理买房是我返回乡村的一种努力”
(树才,诗人、画家,定居大理6年)
去大理买房是我返回乡村的一种努力,因为我老家在浙江奉化,那里的农村山清水秀,物产丰富,但是我又不想回到家乡的农村,我参加过农忙的,割稻,种地,耙地,犁地,这些活我都干过。但大理这个农村很国际化,它是“乡村”,乡村带来审美的东西,有田野这种天然的土地,而且你是土地的主人。
城市的人是没有土地的感觉的,因为泥土全部被水泥覆盖,甚至离水泥地都很远。在城市里,虽然有邻居,但是住在一起几年都不相识,但是农村里,人和人之间有关联。我1983年到京,除了到非洲的七年外,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,但是我没有真正喜欢上城市。农村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离开土地无形的束缚,到城市去。我头十八年的农村生活塑造了我的人格,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回去跟土地建立一种联系。大理满足了我这个心理要求和现实要求。

诗人树才
在大理能放松下来,这对艺术创作和写诗很重要。生活在北京、上海,那种无形的紧张感会给人压力。但是人在放松的时候,这个世界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在大理就是发呆,有时候云就静静地待在天上,有时候动得又很快,那里的山和水让人有一种天地同在的放松感。我住在“山水间”,它在苍山的脚背上,有点坡度,我家地势比较高,从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洱海,从我卧室和书房的后窗,能看到苍山十九峰中的十五六座,这给我凌空居住的感觉。
大理是白族自治州,历史上少数民族、汉族文化融合较多,是大家和睦共存的一个地方,有一种放松、宽容的传统。大理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怪人,艺术家或多或少都是怪人。这个风水宝地,天然地吸引我们这些诗人。大理也有诗人,真正本地的诗人北海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,在人民路下段摆书摊,靠签名售书养活自己,经常驮着一摞书,又买了菜和鸡蛋回家,他也种地,经常在田野里。
06
“以前说回北京,现在说回大理”
(张杨,导演,定居大理22年)
这些年我们在大理经常玩的人,基本上都是1998年认识的。1998年我和刘奋斗一块儿到大理写电影《洗澡》的剧本,除了我们,还有李少红带着郑重、王要两个编剧在这里写《大明宫词》。从那以后,王要、刘奋斗、我,每年都会来大理,形成了一种习惯。我们老来大理写剧本,干脆自己弄一个地儿,以后再来就不用花钱了,其他的朋友来,都可以住在这儿,所以就一人出点钱,有了“后院”。有了这个客栈,在大理就有家的感觉,来得更频繁了。

导演张杨在大理
以前好多人来大理,根本不知道有洱海,来了就在古城,那时候大家对海东的双廊也没什么概念。2009年,我们那一带还没有其他客栈,只有一家叫“海地生活”的客栈。那时候整个双廊可以去的地方,一个是八旬那里,一个是沈见华老师家。再往后有几个更年轻的媒体人来这里。杨丽萍老师每年春节都会回双廊,她们家四姊妹,那时都会回到这里来。那几天我们基本在一块儿,每天晚上坐在一起喝喝酒、聊聊天。旁边一帮小孩儿在那,沈老师的孩子,还有八旬和小四的孩子小彩旗,八旬家的老二八小弟。
我们刚来的时候,大理就那么点人。最初十年都没有太大变化,后来一下子火爆起来,店铺越来越多,一条街上全是游客,大家就从人民路撤走了。但大理的好,是它有无数空间给你,不是说古城没了,你就没地儿去了。实际上,真正喜欢大理的人都没走,二十年过去,我周围最重要的这些朋友都在。
最早我们给自己定位为“云归派”,在北京,我们说自己是从云南归来的一帮人,后来我们定位自己为“云居派”,居住在云南的一帮人,那就不一样了,这里成了家。以前说“回北京”,现在说“回大理”,这里变成更有归属感的地方。
*本文根据《仿佛若有光:大理访谈录》中六篇采访文字摘编而成,为便于阅读,语句顺序有调整。
编辑:红研
好消息:2020全国素质教育新课堂教研成果评选开始了,主要有论文、课件、微课教案评选等。同时开展第十三届“正心杯”全国校园科幻写作绘画大赛。主办单位:《科学导报·今日文教》编辑部、中国中小学教育艺术教与学研究中心、《作家报社》、北京正念正心国学文化研究院、中华文教网等。咨询电话;010-89456159 微信:15011204522 QQ:1062421792 。

相关阅读
-

马华松诗集《黄河颂歌》研讨座谈会在京成功举办
-

笑琰诗歌: 雨润丽水街(外二首)
-

笑琰: 参观安阳曹操高陵有感 (外一首)
-

笑琰: 甲辰秋再访安阳修定寺塔
-

笑琰:甲辰秋问佛安阳万佛沟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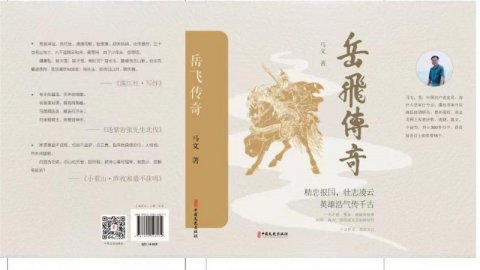
河南作家马文新书《岳飞传奇》出版发行,展现岳飞创心意六合拳
-

诗意人生的感悟与吟唱——略评靳贤孝诗集《信步轻声》
-

诗人作家、书法家靳新国谈写作的奥秘
-

笑琰诗歌:高过天空的是我的灵魂
-

笑琰诗歌:五月,家乡的麦子熟了(三首)
-

商丘辞赋家《刘成宏诗词选集》(第二部/六卷)出版发行
-

全球华人“和文化”文学艺术大展赛展览颁奖系列活动圆满举办
-

笑琰诗歌: 纪念着,怎么就记不清了
-

蔡诗华第15部诗集《日月如梭邮报情》正式出版
-

学者郭谦图书、书法捐赠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
-

军旅诗人王军诗歌6首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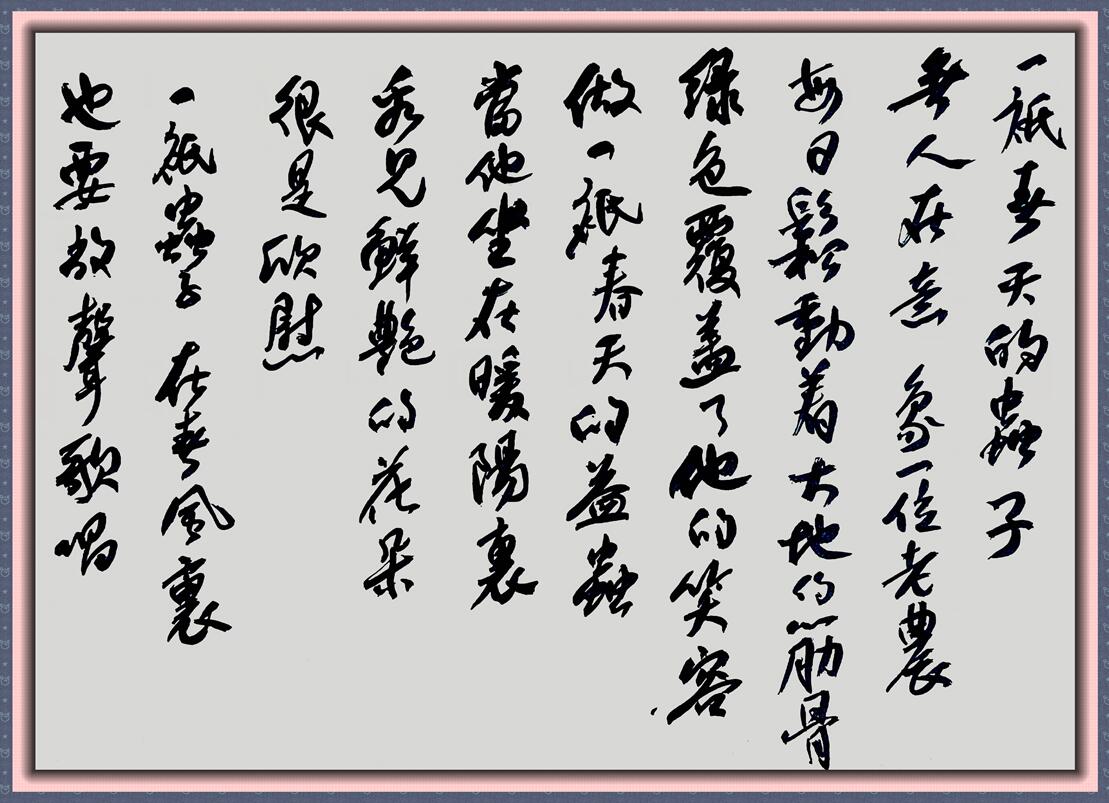
笑琰诗歌两首:与友人一起联欢(外一首)
-

杨维永: 感念程树榛主编 暨《人民文学》的老师们
-

郦道元文学院高研班暨中媒文化艺术交流委员会高峰论坛在安阳
-

“文化学者郭谦图书、书法捐赠仪式”在山西大学图书馆举办
